陈泽奎:文献里的敦煌
敦煌,应该说是一个寄托着为它命名者良好祝福和希望的名字:敦,大也;煌,盛也,这是古人对它的解释,命名者的初心,是希望它能盛大辉煌,繁荣昌盛。
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我们应该把它称之为敦煌元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敦煌这个名字才开始进入中国正史的纪录当中了。
当然,敦煌之名的出现以及所以称之为敦煌,它应该跟武威、张掖、酒泉等河西地名出现在汉代时的情况一样,是遥远的汉朝强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其过程,也当与其他几个地名的出现一样,是汉代人强力奋斗的结果。读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对敦煌自秦汉至清朝之前的有关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秦及汉初为月支、匈奴地,武帝逐匈奴属酒泉郡,后元年(据考证,敦煌设郡的时间不是武帝后元元年,而是早于后元元年。武帝在敦煌设郡的时间应该是元鼎六年)分置敦煌郡,后汉(东汉)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魏、晋时仍为敦煌郡。《十六国春秋》:“晋咸康元年张骏分敦煌等郡为沙州。永和十年祚置商州,仍置敦煌。西凉李暠都于此。北凉得其地,亦治沙州。”后魏(北魏)改为瓜州,并治敦煌郡,后周因之。隋初郡废,仍曰瓜州,炀帝复改州为敦煌郡。唐武德二年改曰沙州,五年又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复曰沙州,天宝初曰敦煌郡,乾元初复故。后没于吐蕃,大中三年张义潮以州归朝,置归义军授之。其后曹义金、曹元德等相继有其地,终五代之季,瓜、沙二州皆附于中国。宋初亦羁属焉,祥符六年沙州曹贤顺入贡,授归义节度使。寻亦附于契丹,天禧三年契丹册贤顺为敦煌郡王。景祐初没于西夏。元初置沙州,寻为沙州路。明洪武二十四年无裔阿鲁哥失里遣使朝贡,永乐三年置卫以授其头领困即来。宣德七年上言诸夷侵掠,愿徙居察罕旧城,不许。正统十一年,其首领喃哥以困于瓦剌,率部属来归,因徙置内地,卫废。
以上的文字,表面上看上去风淡云轻,而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却是波浪壮阔。
从文献记载看,敦煌从汉朝设郡之日起,就与河西其他三郡一样,其命运就与中原王朝的盛衰兴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敦煌随朝代更迭不仅有过名称和隶属的变化,事实上更多地是血与火的洗礼,边关的历史,实际上是血与火铸就的历史。其已知的历史告诉我们,敦煌的设置,事实上和河西其他三郡的设置一样,从其设置之日起,就与其他三郡一起承担起了向西开放、拱卫内地以及连通东西的历史责任,而其地处边陲的地理位置,又让它从设置开始,就打上了浓重的边关色彩。
在汉朝的地图上,敦煌不仅是河西的最西端,事实上也是汉朝西部边关所在,汉时的阳关和玉门关事实上也是通西域入河西的国门,汉及汉以后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敦煌也是其重要的支撑点。因其地处河西与西域的联结点,因而在汉朝开发西域或其后中原王朝经河西通西域、中亚、西亚到地中海的中西交通中的桥梁作用愈益重要,因此从设郡之时起就有了浓重的边关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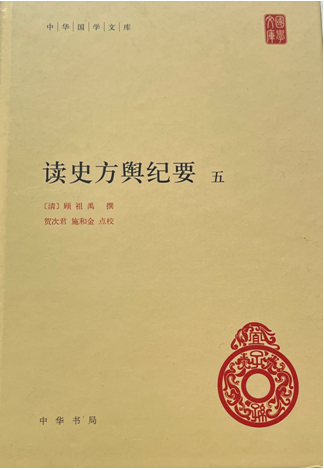
一、 两关通东西
根据史料记载,汉朝对西域的经营的初衷,是始于加强边防拱卫京师的需要。而河西之战的彻底胜利,使得汉朝有了经营西域前提条件。而汉朝对西域的经营的探索,应该是在河西置郡之前就开始了,据《资治通鉴.汉纪》记载,匈奴的浑邪王归降汉朝以后,汉军将匈奴势力驱逐到大沙漠以北,自盐泽(也就是现在的罗布泊)以东,不见匈奴踪迹,前往西域的道路可以通行。于是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曾经出使西域归来的张骞给汉武帝建议说:“乌孙王昆莫本来是匈奴的藩属,后来兵力渐强,不肯再事奉匈奴,匈奴派兵征服,未能取胜,于是远去。如今匈奴单于刚刚受到我朝的沉重打击,而过去的浑邪王辖地又空旷无人,蛮夷之族的习俗依恋故地,又贪图我朝的财物,如果现在我们用丰厚的礼物拉拢乌孙,招他们东迁,到过去的浑邪王辖地居住,与我朝结为兄弟之国,他们势将听从我朝的调遣,听从了就等于断了匈奴的右臂一般。与乌孙结盟之后,其西面的大夏等国也都能招来成为我朝的藩属。”汉武帝认为有理,便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每人马二匹,以及数以万计的牛羊和价值数千万钱的黄金缯帛,又任命多人为手持天子符节的副使,沿途如有通往别国的道路,既派一副使前往。
张骞到达乌孙之后,乌孙王昆莫接见了他,但态度十分傲慢,礼数不周。张骞转达汉武帝的谕旨说:“如果乌孙能够向东返回故土居住,那么我大汉将把公主许配给国王为夫人,两国结为兄弟之邦,共同抗拒匈奴,则匈奴不能不破败。”然而,乌孙自己因距汉朝太远,不知汉朝是大是小,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匈奴的藩属,与匈奴相距又近,朝中大臣全都畏惧匈奴,不愿东迁。张骞在乌孙呆了很久,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便向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附近各国分别派出副使进行联络。乌孙派翻译、向导送张骞回国,又派数十人、马数十匹随张骞到汉朝报聘答谢,乘机让他们了解汉朝的大小强弱。这一年,张骞回到长安,汉武帝任命他为大行。一年多以后,张骞所派出使大夏等国的副使大部分都与该国使臣一同回来,这样,西域各国就开始与汉朝联系往来了。
这些记载明确了,在汉朝在河西置郡之前,事实上汉与西域的交往巳经开始了。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许多变化,促使汉朝有了在河西置郡的想法。据史料记载,汉通西域的初衷,是想说服原居于敦煌一带的乌孙人返回故土与汉朝一起,共同对付自己的强邻匈奴,但已经习惯了在西域生活的乌孙人已经没有了返回故土的意愿了,汉朝只能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史书记载,“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既然乌孙王不肯东还,汉朝便在浑邪王旧辖地区设置酒泉郡,逐渐从内地迁徙百姓来充实这一地区。以后,又从酒泉分出部分地区设置武威郡,用以隔绝匈奴与羌人部落的联络通道。由此,我们知道两个情况,一是汉通西域的活动早于汉朝在河西置郡的年代,二是汉在河西置郡既是为了填充没有乌孙人之后河西边防的空缺也是为了保证中原和富庶的西域交往的通畅。因此我们知道,为了达到占有河西、西通西域的目的,置郡设关,对汉王朝而言,也就成了不二选择。这当中,阳关、玉门关的设置,既是对保证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的一种需要,也更是关键。
《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从玉门、阳关前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从鄯善沿南山北麓前行,顺着河流向西到莎车,是南道;从南道向西越过葱岭,就到了大月氏、安息。从车师前王廷顺着北山沿河流西行到疏勒,是北道;从北道向西越过葱岭,就到了大宛、康居、奄蔡。以前,西域各国都受匈奴统治。匈奴西部的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统辖西域各国,常驻于焉耆、危须、尉黎一带,向西域各国征收赋税,掠取各国的财富。


由此,我们知道,阳关、玉门关的位置的战略价值本身就是存在的,而汉朝在此设关立卡,事实上就是扼住了中原通西域的咽喉,事实上也扼住了通西域和南出联系羌人的咽喉。这不仅保证了汉朝战略目标的达成,也为中原与西域到达欧洲开通了陆上通道,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敦煌置郡和两关的设置,既是中西交通有了保障,也成了许多人建功立业的新通道。史书记载,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取得成功之后,通西域成了许多人实现人生梦想的热途。史料记载,自博望侯张骞因出使西域而获得尊贵的地位之后,他的部下争相上书朝廷,陈说外国的奇异之事和利害关系,要求出使。汉武帝因西域道路极为遥远,一般人不愿前往,所以听从所请,赐给符节,准许招募官吏百姓,不问出身,为他们治装配备人员后派出,以扩大出使的道路。这些人返回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偷盗礼品财物或违背朝廷旨意的现象。汉武帝因他们熟习出使之事,所以治以重罪,以激怒他们,让他们立功赎罪,再次请求出使。这些人反复出使外国,而对犯法之事看得很轻。使臣的随从官吏和士卒也每每盛赞外国事物,会说的被赐予正使符节,不大会说的就封为副使。因此,很多浮夸而无品行的人都争相效法。这些出使外国的人都是贫家子弟,他们将所带的国家财物据为私有,打算贱卖后私吞利益。西域各国也厌恶每个汉使所说之事轻重不一,估计汉朝军队路远难至,就拒绝为汉使提供食物,给他们制造困难。汉使在缺崐乏粮食供应的情况下,常常积怨,甚至和各国相互攻击。楼兰、车师两个小国,地处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上,攻击汉使。王恢等尤其厉害,匈奴军队也时常阻拦袭击汉使。使臣们争相报告朝廷,说西域各国都有城镇,兵力单弱,容易攻击。于是,汉武帝派浮沮将军公孙驾率骑兵一万五千人从九原出塞二千余里,至浮沮井而还,又派匈河将军赵破奴率骑兵一万余人从令居出塞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目的是为了驱逐匈奴,让汉使不受阻拦,但没有遇到一个匈奴人。于是分割武威、酒泉二郡土地,增设张掖、敦煌二郡,迁徙内地民众充实该地。
因为有了敦煌与两关的支撑,自然带来了交通的繁忙和两关的繁荣。史书记载,“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从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汉武帝得到大宛出的汗血马,非常喜爱,命名为“天马”,去大宛搜求的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汉朝出使外国的各个使团,大的一行数百人,小的一百多人,所带礼品等物与张骞出使时大致相当,以后随着对西域情况的日益熟悉,使团人员及携带之物也逐渐减少。大约在一年之中,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者,多时十余批,少时五六批;其中路远的要八九年,较近的也要数年才能回来。由此我们知道,汉武帝时期,从汉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前往西域的使团、商人或是西域到长安的使团商人应该是不绝于途,两地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很频繁的,两关的出入接纳自然也很频繁,由此也可以看出,承担着保障东西交通畅达的敦煌和两关的地位的重要性。
如今,因为历史原因,因为时过境迁,阳关、玉门关曾经的繁忙与辉煌已经远去了,曾经威严的国门的雄姿也难见其真容了,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它曾经的荣光与曾经在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今,当我们在阳光和玉门关的遗址上凭吊时,在辽阔的戈壁、黄沙的映衬下,也还能依稀感受到它们当年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二、 人才显底蕴
而敦煌值得我们关注的,这里不仅是边关重地、交通要道、丝路隘口、国际都会,敦煌自设郡之日起,人文荟萃应当更值得关注。

第一个系统研究敦煋的人当属刘昞。刘昞,字延明,敦煌人,《魏书》有传,是五凉时期重要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据本传记载,刘昞早年师从河西大儒郭瑀学习,历仕西凉、北凉、北魏三朝,是五凉时期河西著名的学者,从政之余,潜心学术,著述颇丰,而在其众多著述当中,与敦煌直接相关的著作,当属《敦煌实录》。《敦煌实录》既是刘昞曾经传世的著作之一,也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系统研究敦煌历史和人文的重要著作和重要的文献,只可惜在传世的过程中散佚严重,原本二十卷的著作,我们能看到的原作,只有一卷而已,而且应该是残卷,并非完整的一卷。
第二个系统研究敦煌之人,当是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凉州人张澍,由他辑录而成的《续敦煌实录》是他对散佚严重的《敦煌实录》的一个整理成果。《续敦煌实录》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对《敦煌实录》的续补,而实际上则是对《敦煌实录》中有关敦煌历史人物的重大拓展。这不仅从《敦煌实录》和《续敦煌实录》的篇目,而且从内容上都可以看出来,如现存的《敦煌实录》只有一卷,而《续敦煌实录》则多达五卷;时间上,《敦煌实录》仅限于北魏以前的敦煌的情况,而《续敦煌实录》则拓展至张澍能看到的文献当中有关《敦煌实录》的文字;内容,《敦煌实录》收录的人物约20人,而《续敦煌实录》则扩张至120人之多。也因此,《续敦煌实录》的点校者、甘肃著名学者、西业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鼎文先生称《续敦煌实录》的辑录者张澍为今日之显学敦煌学研究之第一人。
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不论是《敦煌实录》还是《续敦煌实录》,它们值得让我们关注的是,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了解曾经活跃在敦煌历史上的那些历史人物的可资依凭的历史记录,而透过这些记录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遭际和各自不同的人生过程,更让我们看到了敦煌这片土地上本来该有的生活以及适应当地生活的当地人的人文样貌。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人,人的生活状态才是一个地方生活的最基本最真实的反映。敦煌历史上曾经的风云际会,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了和他地不一样的生活样貌。
三、 新学放异彩
这里我们说敦煌的“新学”,自然是指敦煌学。
光绪二十六年亦即公元1900年,这一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悲催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第二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开始,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时代。而也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离京城遥远的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也发生了一件令世人瞩目的事情,敦煌莫高窟的主持人王圆箓在无意中发现了在其后震惊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因机缘巧合的面世,一时成为学界的热搜,一门显学——敦煌学由此产生。也因此,这一年,我们应该称它为现代敦煌学元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历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了世界范围内学术界持续研究的课题。

敦煌学的诞生,应该首先是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书或文献的发现。而敦煌学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显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书或文献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流布。敦煌文献流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术研究开始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个伤心的过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甘肃人民出版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名叫《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的书,这本由英国人彼得.霍普科克撰写、由我国学者杨汉章先生翻译、由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作序的著作,真实地记录了1949年之前,俄国的柯兹洛夫、奥布鲁切夫、克里门茨,德国的德兰、范莱考克,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的华尔纳等人,打着探险、考察、游历的招牌,在我国古丝绸之路的西域地段(我国的新疆地区,包括敦煌在内),到处发掘、盗取地下文物的情况,其中直接染指敦煌遗书及其他文物者,著名的就有斯坦因、伯希和、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华尔纳等。由此,我们可知敦煌文献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布的一般情况。而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开始流布至今的一百二十多年来有关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学界的研究广泛而深入,已成洋洋大观,各种著述,虽然不能说汗牛充栋,但用车载斗量来形容应该不算夸张。单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即现如今的读者出版集团所出版的有关敦煌学类的出版物,各种版本各种品类,加在一起,应该不少于二三百种。由此可见其研究盛况。当下,因为互联网的关系,现如今有关研究的盛况的检索十分方便,因此,这里恕不赘述。
当然,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敦煌学的研究,从初开始的敦煌文献的研究,逐渐拓展成包括石窟、艺术、历史、文学、考古等多个领域的多学科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敦煌在甘肃,而敦煌学则是世界的欣喜局面。
在这里,我们应该铭记的是,敦煌学的诞生,得益于文献,得益于石窟,得益于古人的创造;而敦煌学的发扬、光大,则得益于学人们的持之以恒的潜心研究和弘扬,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学术禁锢消除和国际及地区间学术的交流的通畅。也因此,敦煌以及敦煌学,诚如其名字一样,敦大煌盛,其过去有辉煌,而未来仍可期。
(部分图片来源:百度)
版权声明:
凡文章来源为"兰州新闻网"的稿件,均为兰州新闻网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兰州新闻网",并保留"兰州新闻网"的电头。如本网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